- 热搜词
糖果派对下载-档案:不只为当代艺术留痕~
基于当代艺术背后不断更迭的历史语境与社会背景,其反映的思潮与文化态度也处在一个持续变动的境况之中。在今天,当我们的艺术评价体系还无法对掺杂着各种观念和现象的当代艺术给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时,将它们如实且全面地记录下来就成为了一件必要且重要的事情。近年来,以档案记录当代艺术创作、展示和传播的现场,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美术史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审视当代艺术发展动态的独特视角。档案,如何成为一种观察和理解艺术的途径?其自身所带出的多重工作方法与观察视野,又能为当代艺术带来哪些新的认知及实践拓展?
如果从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公园举办的“星星美展”开始算起,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了42年的历史。这期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记录与书写多种多样,留下了很多文献与资料。进入21世纪,当代艺术的发展在资本的推动下快速生长,双年展、大展与个展比比皆是,公私机构和个人都在举办当代艺术展览,但是展览过后留下了什么?
“年鉴”思维:
记录变量而不是常量
如何把握这些稍纵即逝的现象、群体和意识,并对之进行有效的保存、梳理和呈现?于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献和档案工作应运而生,运用“年鉴”的思维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一年中当代艺术展览、事件、人物与资料,并且以展览的形式向大众展示,这便是由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自2015年开始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以下简称“年鉴展”)。这个至今已连续举办6届的系列展建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借助于编写《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的成果予以集中呈现。面对一个以“年鉴展”为名的当代艺术展,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或许不是具体的作品本身,而是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语境、理念与方法。
受疫情影响,被推迟举办的2019年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并没有选择此前5年的固定展示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而是选择在深圳坪山美术馆与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两地联动举办,并与北京798艺术区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馆的网络展构成呼应关系,这似乎预示着当代艺术的一种处境,也反映出年鉴展的意义并不在于展览本身,而是一种对于时代发展进程的镜鉴。站在2021年回看2019年年鉴展,朱青生说:“展览的意义在于观众可以在疫情中看到疫情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发生的事情,而艺术家在疫情中和疫情前的反应则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这个展览有点像化石,或者是一个凝固了的标本。”
梳理档案便是在建构历史。那么,仍在进行和发生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言史?在朱青生看来,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并不存在“历史”,但它具有“历史工作”的特点——对所发生之事件和现象的记录,形成档案,及时和适时地给出尽可能全面和客观的报道。据统计,2019年《年鉴》共收录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和活动 3941个、文献4319篇、15000多个艺术家的活动信息。根据这些数据和信息的归纳,《年鉴》学术团队最终选出107名(组)艺术家来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动向。
在2019年“年鉴展”现场可以看到,艺术的当代性、艺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艺术与科技、女性/性别艺术、艺术群落的变革、当代艺术策展、“网红展”、艺术乡建等问题延续了前几年的发展势头,继续受到较多关注。另外,当代艺术的国际化、替代空间、当代艺术与“潮文化”的结合、艺术版权等问题由于一些特殊事件、现象的发生,引发了集中的讨论。
“《年鉴》的目的是捕捉变化,记录变量而不是常量。”朱青生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和方法,“年鉴展”的叙述上定位于“新”,旨在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各个重要事实的意义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以2019年“年鉴展”为例,在论述艺术的当代性时,策展团队首先总结了技法和材料在当代艺术中所呈现的变化。从当代艺术家群体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不断反思传统艺术门类的边界和法则,对于传统文化资源,并不完全排斥,也尝试构建新的形式上的自洽。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传统思想更多与个体经验相关,厚重的历史叙事在作品中的比重正在降低。其次,就现实的当代性而言,作品除了反映中国当今社会的多元性,在一些创作中,一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被引进。此外,虚拟网络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中固有的层级关系,一些影响社会固有观念的技术被运用到了创作中,挑战了私密与公共的传统界限。
策展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徐志君说:“‘年鉴展’不是告诉大家什么最能代表中国的当代艺术,而是用一种‘提示’的姿态,帮助记录中国当代艺术现场发生变化的过程,一两年的变化可能并不突出,但是从更长的时间角度来看,会看到艺术现场的变革轨迹。”在徐志君看来,“年鉴展”是在《年鉴》框架下重构感官的行旅,实际上是重构一个艺术现场的过程。而这正是“年鉴展”策展首先需要面对的困境,即如何在文献的框架和现场体验两端寻求一个平衡。
在遴选艺术家方面,“年鉴展”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在数据库之上的计算来选择艺术家,究竟是根据何种计量方法我们无从得知,但显然这种量化的指标接近当代艺术评价的“客观”。徐志君表示,事实上,它是一个未完成的尝试,在探索一种展览可能性:策展人是否可以不那么强势地介入展览,以稍微“弱”一点的方式完成一个展览?
在游弋的档案中
扩展思想的边界
近年来,在当代艺术展览现场中,以文献作为展览主体的文献展已然成为了一种现象。然而,展览中的档案如何才能突破作为陈列品存在的局限,打开更多的讨论和实践可能?围绕“中国革命的视觉档案”计划,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负责人高初及团队在过去数年间抢救性地收集、整理、保存了大量中国革命的摄影档案,并在档案的汇集与整理、研究与教学、展览与出版等方面摸索出一套整体性的工作方法。
面对诸多需要被考证和激活的影像档案,档案工作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我们面对的图像和图像的历史说明,从拍摄开始就一直在变动之中,每往前追问一点,其实都能激活一些很微妙的东西,极大地改变着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并由此打开一个新的缝隙。”高初介绍说,当把不同的档案放在同一时间轴线上去对比时,会发现非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说延安时期留下来的摄影,和人们看到的前线边区和战场的摄影是很不一样的。再比如抗战时期,除了中共的摄影师以外,当时还有包括国民党摄影师、日本摄影师以及国际观察员在内的不同摄影团体集聚在战场上。这些摄影群体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交错于同一空间,他们所做的不光是在艺术上实现新的可能性,也在创造着另外一套意义系统和工作机制。
如何将档案转变为研究的经验?高初分享了团队通过口述史激活图像的感悟:口述史是一个互相信任、把个人的感受和档案馆里的资料碰撞在一起的过程。这个研究过程是在探索如何使机构档案变得有意义,而其中家庭史和生命史最终压过了机构档案,成为更有价值的发现。“当我们以历史的工作方式,将物件和信息弥合在一起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某组照片是由哪位摄影师拍下的,摄影师是如何从一个战斗到了另一个战斗,慢慢地,我们还看到了拍摄者变化的视角、逐步成熟的技术、渐渐凸显的个人的风格,而这样的风格又传递给了谁……这才是摄影史研究的起点。”高初说。
显然,档案自带了一套工作体系,并且档案工作的方向感往往比知识生产的方向感来得更有效,它会把你带去真正值得做的方向。当一张照片可能产生的效果不再是历史的见证,而成为历史动能的时候,它能组织的就是数以亿计的观看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摄影文献,还是当代艺术文献,都有机会在游弋的档案中不断地将思想边界扩展至希望的方向。
保持历史的距离
提供反思的“入口”
在亚洲艺术文献库资深研究员翁子健看来,文献工作不只是档案的编目和保存,更多是在于内容的不断发掘和深化。而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档案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同一条脉络上完成的,且研究先行。从研究到档案,亚洲艺术文献库在20年的发展中逐步探索出七大重点议题:艺术书写、地缘、展览历史、承故纳新、教学、行为艺术以及女性艺术。
亚洲艺术文献库对文献的分类方式相对比较简约,翁子健说,从研究的观点看,分类就是判断。对于一个文献库来说,应该尽可能减少先导性的判断。“类似‘观念主义’‘女性主义’或者‘现代艺术’‘当代艺术’这些分类法,本质上是艺术史判断,而艺术史又很擅长推翻和重构那些在过去被确认的定义,所以,从艺术史的角度对档案进行分类,很容易造成误解,或让人怀疑。我们更希望用尽量中性的方式,不去影响研究人员的判断。”
此外,翁子健认为,档案的活化也十分必要,可以以新的阅读视角调动馆藏档案,组织艺术活动,为研究领域提示出新方向的开端。但同时他们在实践中较少直接去讨论当下的情境,“记录当下固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但是,它的工作量极大,也涉及到一种不一样的研究逻辑。从书写历史的观点出发的话,我们需要‘历史的距离’,也就是说,事情往往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呈现出它的历史意义——它后续的发展如何?它跟当下有没有关系?有这样的距离,我们才能更好地辨认出历史的对象,找到研究的思路。对于文献库来说,针对历史,使我们的工作范围也变得十分明确。” 翁子健说。
作为一个游弋于研究、策展和创作交叉地带的研究者,于渺的工作往往从指认跨国档案的缺失、矛盾和不均衡出发,在档案之间建立多重的空间或地理关系。2017年,她在广东、巴黎、柏林三地策划的展览“潘玉良:沉默的旅程”就是缘起于现藏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摄影档案“马克·沃尔档案”,档案的构建者马克·沃尔是巴黎的一个民间摄影师,于一战结束后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地区开了一家照相馆,他的顾客群体主要是当地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从1920年代直至1970年代,他陆续拍摄了20万张玻璃底片的照片,在这个庞大的档案中就包含潘玉良。潘玉良和徐悲鸿同为第一代赴法留学的中国艺术家,然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潘玉良缺席于新中国美术,介于中国现代美术和西方艺术经典之间的她遭受了国内、国际上双重他者化和双重失语的状态。她的大量带有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带有跨种族情爱欲望的画作很难被“爱国女艺术家”等标签简单收纳。虽然拥有巨大声名,但是她依然是马克·沃尔档案中的“无名艺术家”。
如何梳理关于潘玉良的艺术档案?策展的第一步便是建立一种研究型的合作关系,参展艺术家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对潘玉良的作品馆藏、档案和历史遗迹进行一系列跨国探访,包括安徽省博物院、上海老弄堂、巴黎国立美术史图书馆、巴黎警察局等地。“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藏品和档案所携带的历史信息,还有其所处的空间、建筑、管理者、机构语境、与其相邻和并置的都有什么。这个过程中,潘玉良终于慢慢显影,而我们也接受这些都只不过是关于她漫长生涯的一串串碎片。艺术家们在展览中呈现的创作都是基于对于档案片段的重组、想象、拼搭以及虚构。当我们以不同方式将潘玉良的作品和人生投射入我们当下的个人轨迹时,‘潘玉良:沉默的旅程’最终成为一场多声道的混响。”于渺认为,档案无论作为手段还是形式都在试图召唤无法被简约化的历史,将其投射至当下以开启新的对话。档案间的“幽灵”作为一种感性的经验不仅仅是获得历史感知的媒介,往往也是反思当下的入口。
显然,档案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它有着不同的深度、维度、针对性和方法。面对流淌不息的艺术长河,当代人有责任按下快门,把信息凝固下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即时的参照。朱青生说:“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活动、一种精神,其实未必非要是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它也可以是普通的材料或者档案。我们的工作就是对自认为是当代艺术的活动进行持续性记录,为时代留下一份档案,这个档案记录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也是这个时代的人的情况,或许这正是当代艺术档案的意义所在。”
-
 12bet下载:被曝花钱代写代发论文的党校副教授,曾发论文100多
12bet下载:被曝花钱代写代发论文的党校副教授,曾发论文100多
-
 凯发线上app下载网址:三峡船闸单日通过量创历史新高
凯发线上app下载网址:三峡船闸单日通过量创历史新高
-
 下载萄京娱乐场app:肯德基、麦当劳连这个都开始收费了!网友炸
下载萄京娱乐场app:肯德基、麦当劳连这个都开始收费了!网友炸
-
 威尼斯人app下载苹果:韩国前国务总理李汉东去世,享年87岁
威尼斯人app下载苹果:韩国前国务总理李汉东去世,享年87岁
-
 威尼斯人app官网下载:印度安得拉邦一采石场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
威尼斯人app官网下载:印度安得拉邦一采石场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
-
 云顶国际手机版下载:瞭望·治国理政纪事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云顶国际手机版下载:瞭望·治国理政纪事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
 亚博app下载官网下载:武汉黑科技精品闪亮首届消博会:智能机器
亚博app下载官网下载:武汉黑科技精品闪亮首届消博会:智能机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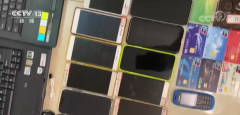 威尼斯人下载app:“跑分”“菜商”“水房” 电信诈骗黑话大揭
威尼斯人下载app:“跑分”“菜商”“水房” 电信诈骗黑话大揭
-
 汇赢网软件下载wx30 com:灵感来自晨练老教授,话剧《家客》即将
汇赢网软件下载wx30 com:灵感来自晨练老教授,话剧《家客》即将
-
 亚博app下载安卓版:昌平区回龙观街道回龙观新村社区探索实行“
亚博app下载安卓版:昌平区回龙观街道回龙观新村社区探索实行“
-
 韩国瑜复出布局 名嘴陈挥文:要想通3件事02-19
韩国瑜复出布局 名嘴陈挥文:要想通3件事02-19 -
 1欧元甩卖王室城堡给政府,德国汉诺威王子被父亲起诉02-19
1欧元甩卖王室城堡给政府,德国汉诺威王子被父亲起诉02-19 -
 因疫情连失亲人打击不断 美国民众欲哭无泪02-19
因疫情连失亲人打击不断 美国民众欲哭无泪02-19 -
 美国前女主播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官方未公布死因02-19
美国前女主播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官方未公布死因02-19 -
 男子抓拍举报占用应急车道18起!交警:已全部录入02-19
男子抓拍举报占用应急车道18起!交警:已全部录入02-19 -
 杨幂胸前大深V直播 肩带撑不住北半球露出来了02-19
杨幂胸前大深V直播 肩带撑不住北半球露出来了02-19 -
 电影票房破亿 女星脱了全裸辣送福利网嗨爆02-19
电影票房破亿 女星脱了全裸辣送福利网嗨爆02-19 -
 印军高官鼓吹边境对峙“获胜” 分析人士:为莫迪政府“政治减02-19
印军高官鼓吹边境对峙“获胜” 分析人士:为莫迪政府“政治减02-19 -
 海南离岛免税店春节销售额超15亿元02-19
海南离岛免税店春节销售额超15亿元02-19 -
 三明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02-19
三明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02-19









